王世襄藏品不负京城第一玩家名号 所收皆“邪”(2)
王世襄八十寿辰时,妻子袁荃猷特意为他刻制了这幅《大树图》。圆形树冠上,王世襄的十五件爱好像十五枚果实悬于树冠之中。漆器、家具、竹刻、绘画、铜佛、鸽子、蟋蟀、蝈蝈、大鹰、獾狗等,巧妙贯穿王世襄一生所“玩”。
“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在生前文字中,王世襄总结自己玩好。
“畅老(编注:王世襄字“畅安”)玩的东西都比较‘邪’。架鹰驯狗,放鸽蓄虫,即使在世家读书子弟中,他也称得上‘另类’。”文化研究者、《旧时风物》一书作者赵珩说,“其实畅老喜欢的那些很多是特别市井的,但他没有偏见。”赵珩说,当时京城世家子中,比较洋派的都是去舞场这样的地方,而王世襄喜好的东西其实有不少是挺辛苦的。“熬鹰、捉獾都很费力气,有的半夜两三点就得起床,像驯鹰为了让鹰落到手上,得把手掌裹满了布才行,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
王世襄也常常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赵珩记得常常在王世襄家中见到各色民间工匠,王世襄和他们谈匏器、讲鸽子,“聊天时候的兴奋溢于言表,就像回到青少年。”
年轻时的王世襄玩得很“野”。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后,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被老师洪业称作是“未知数”。他在校外的住处与考古学家陈梦家与翻译家赵萝蕤夫妇相邻。有一次深夜,陈梦家夫妇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以为有强人到来。其实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王世襄的玩性之大可见一斑。
“但你说他是玩儿家,我始终不太同意。他把过去不入流的东西,玩得非常精到,这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在赵珩看来,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荒嬉,王世襄玩到追本溯源。“玩物”实际上是“研物”。
王世襄抓蛐蛐、养蛐蛐、斗蛐蛐,也写《蟋蟀谱集成》,写的关于蛐蛐的《秋虫六忆》被黄裳认为是最好的散文。张中行曾经回忆一次造访王世襄家,谈到蛐蛐罐,王世襄登高,从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蛐蛐罐,让他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屋内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北京旧称)。临辞,王世襄送他一部新出版的《蟋蟀谱集成》。回来路上张中行禁不住慨叹,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张中行末了说,“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
“他这一辈子能干的事情很多,中学西学的融会贯通,少年时在美国学校学习,英文非常好。虽然旧家出身,他没有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走那个路子,中年时期又赶上我们极左的政治环境,他的青少年时代和中年时代都是被否定的。”赵珩一直认为,王世襄的中年本应该是继《国画论研究》的完成之后,做出更大的成就。可惜自1952年之后,直到80年代中期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和《髹饰录解说》出版之前,竟沉寂了近三十年时间。
在沉寂的三十年里,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被打成过“右派”。因为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职责是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但这一有功之事在“三反”中却被诬为贪污盗窃国宝,没有证据被释放,但还是不明不白被故宫辞退。赵珩说王世襄生性达观,但这件事却是他一直到晚年都耿耿于怀的事。
戴眼镜、光着腿牵一头牛,此次展出的一幅《牧牛图》是王世襄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时期的写照。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即使生活艰苦,王世襄还是找到了玩的乐趣。“他向当地渔民学打鱼,还摆鳜鱼宴。”赵珩的父母当时也在咸宁的“五七”干校,鳜鱼一毛六分一斤,善庖厨的王世襄用14条公鳜鱼做了一桌菜:炒鳜鱼片、炸鳜鱼排、糖醋鳜鱼,还有干烧鳜鱼、清蒸鳜鱼和清汤鱼丸,其中一道“糟溜鳜鱼白加蒲菜”是王世襄最得意的香糟菜,“现在一个饭馆哪里找出14条活鳜鱼来做一个菜?”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现在一说中式都觉得繁复为美,很少人能够体会简洁的美。”田家青说,“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其实是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精髓的体悟。
展览中,一张“鲸背象足”的花梨独板面大画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是王世襄和弟子田家青按照明式家具特点自己设计制作的画案。以明式家具研究著名的王世襄研究了一辈子明式家具,一直希望把他的思想融入在一件家具中,在2002年终如愿以偿。王世襄《锦灰堆》、《自珍集》等为人们喜爱的著作都是这张大案上完成的。中国古典家具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惟一入室弟子田家青说,也是在这件家具中,淋漓尽致地融进了他“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的审美境界。
“简洁的东西是最难做的,就像写书法,比划少的最难写。”田家青说,这件画案做出来之后,陆续有不少人按这个样子做,但都仿不出那个神气。“制作古式家具,如果只是原样照仿,只要把结构做对、把工艺做精,再现其形体外貌并不算太难。难的是把握古器的风韵,令其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田家青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南方友人郭先生在其经营的进口花梨木材中开出了一块尺寸硕大的板材,质地细密,无疤无裂,十分难得。1995年,郭先生来京看望王世襄先生,得知王老已将过去一直使用的那张明代紫檀大画案交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自己却将就用着一张从家具店买来的“大班台”。感动之余,执意将此料送与王老,并希望田家青能帮着打造一件大案,以替代原物。
相关阅读:
网友评论:
- 鉴赏把玩
- 核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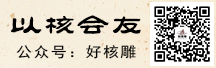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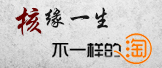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