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藏品不负京城第一玩家名号 所收皆“邪”(3)
于是根据木材特点,构思设计,确定榫卯结构和工艺方案,两块木料既要得到最大限度的物尽其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此外大案采用活插结构,所有部件都是靠榫卯“斗”合,无钉无胶。全法明式,但更加重明式特点,王世襄脑中存在多年的一张大案形象逐渐成型。
打造此案的场地在北郊,田家青记得,王先生有时候一早乘早班郊区车赶到,先与大家一块吃早饭:棒渣粥、馒头、细酱萝卜丝儿,点上自制的香油。饭后一同切磋。大案制成后,长近三米,重近半吨,王世襄特作案铭,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以石青填色,记述了大案设计打造过程,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田家青认为是点睛之句。
“现在一说中式都觉得繁复为美,很少人能够体会简洁的美。”田家青说,“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其实是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精髓的体悟。“明式家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是好的明式家具,我说,你拆不了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就是它没有为装饰而装饰的部件。”
在田家青看来,王世襄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干实事,不务虚。他记忆中王老一个生活细节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朋友们来请王先生吃饭,往往去的都是比较高级的酒店,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往往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先拿筷子把菜里边做的虚的东西,什么萝卜花啊,雕的仙鹤、小桥,放的花瓣—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的王世襄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完全下意识地给它挑出去。”
随遇而安,其乐不辍
赵珩感慨,我们看到这些过去的器物,之所以怀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里面装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平淡、踏实、安静,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格格不入的那些品质。
“不是畅老发生了改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发生了改变,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包容的时代。”赵珩觉得这20年来,或许是因为“文物热”升温,王世襄、朱家溍这些人的名字才为人所熟知、追捧,关于他们的书籍、画册出版了不少,个人经历更是被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并被誉为“奇人”“泰斗”“名家”,他们一生为文物鉴定所做出的贡献才为人赞颂。“其实,这些先生的人生经历都并非顺畅。但关键是像畅老,能做到随遇而安,其乐不辍,一直到晚年。”
“有人称他为‘玩儿家’,我总以为说得太轻浮了些。过去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畅老最为擅长的木器、漆器、匏器等杂项之学,都不算显学,但在他手里却是绝学。”赵珩说。
王世襄好友、文博大家朱家溍曾说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像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中国漆器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但关于漆器的著述却仅有一部《髹饰录》,而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也就成为唯一注释和阐述《髹饰录》的力作。他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更是一部千百年营造匠作的经验总结。或者换言之,正是有了他的《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北京鸽哨》这些著作,这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赵珩说。
“对他热爱的那些器物,如家具、葫芦器等,他后来倒有了某种乐观。”北大中文系学者王风说。王风因古琴与王世襄和袁荃猷结缘,在王老后面几年常过去陪他说说话。会传统手艺的老师傅们先后去世,原先也会有担忧,但市场利益的推动,各自形成行业,有的仿制几可乱真,甚至有所谓葫芦一条街,转而作假、走私成了乱象。“我是功过难定”,王世襄曾经对王风说笑。王风觉得,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王先生在不绝如缕的时候接一把手,结局可真不好说,他就是那根“缕”。
“他不是那种怀旧的人,有的东西没有希望也就放弃了,譬如说美食。”最直接的影响是不下厨了,因为食材不对,什么味道都不对。王风记得有时王先生留饭,就到周围小馆子,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点菜,并不征求意见,然后详细交待厨师该如何做。
前几年的时候也还有坚持,赵珩记得东直门外十字坡开了一家点心铺,叫做荟萃园,汇集了旧京许多老字号的传统点心,王世襄专门打电话给赵珩父亲。“王世襄的话是不会错的。”果真,那时荟萃园刚刚开张,确是很地道,像奶油萨其玛、翻毛月饼、奶油棋子儿之类,都很不错,当时店铺内还悬挂着畅老为荟萃园的题字。“只可惜昙花一现,不到两年就歇业了,有的东西找不回来了。有好的食客才有好的厨师,就像有好的观众才有好角儿。”
“畅老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我现在慢慢步入老年,也开始体会到了。我们说‘这个东西没有老味儿’,狭义上讲的是味道口味,但英文是taste,有一个时代的烙印和氛围在里面。”赵珩说,肯德基麦当劳可以标准化,但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都是个性化的,没法做到标准化。
“其实我们今天怀念畅老,并不是说今不如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遗憾。”赵珩感慨,我们看到这些过去的器物,之所以怀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里面装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平淡、踏实、安静,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格格不入的那些品质。
譬如王世襄还在世的时候,赵珩曾经听王世襄和营造学社另一位还健在的罗哲文老先生聊营造学社的事。王世襄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经梁思成介绍,在营造学社做助理研究员。抗战期间,营造学社迁到四川重庆李庄,大伙儿穿着背心,在唐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上做测绘。“那时候物质生活多艰苦,但是能苦中作乐,勤奋敬业。”
相关阅读:
网友评论:
- 鉴赏把玩
- 核雕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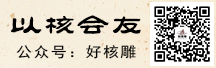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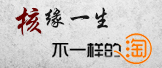

 返回顶部
返回顶部



